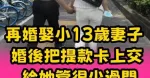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心字香燒完整後續

2/3
「阿兄,我想回家。」
阿兄自然沒辦法帶我走的。
我們都心知肚明。
就算如今是富甲一方的商人,也沒辦法帶走皇帝的嬪妃。
我們只能坐在這四四方方的宮牆裡,回憶著曾經的好光景。
他絮絮講著我幼時的趣事。
我彎著眼睛,笑了又笑。
直到太監來催,說時辰已到,阿兄該回了。
我才戀戀不捨地鬆開阿兄的袖擺。
「明日,阿兄還來麼?」
未等阿兄說話。
身後,忽然傳來一道陰惻惻的聲音:
「他明日不會來了。」
「這次進宮,乃是朕格外恩准。」
我回頭,蕭瑄正從花架後緩緩踱步而出。
不知道待在那裡,偷聽了多久。
他扯了扯唇角,笑意嘲諷。
「姜楚,朕從前倒是從來不知道,你與他這般情深意重。」
「你若想要實現什麼心愿,該來求朕才是。」
10
阿兄走了。
蕭瑄被我嘲諷了一通,也怒氣沖沖地走了。
這天夜裡,又淅淅瀝瀝下起了雨。
半夜,殿門被人猛然破開了。
黑暗裡,有人摸到了我的榻邊。
潮濕的熱氣吹拂在我耳廓上。
那人壓在了我的身上。
春芽尖叫著要跑去喊人,被踹到地上。
「楚楚。」
燭火亮起,映出蕭瑄有些疲憊的面容。
他身上都是潮濕的水汽。
難聞的酒味鑽進我的鼻尖。
蕭瑄抬手抱住我,夢囈似的喃喃:
「不要再說氣話了,你不知道朕聽了那些話,難過得很。」
「和朕和好,好不好?」
說著,他的手在我腰間亂摸。
竟是要解我的衣帶。
我抬手,甩了他一耳光。
「滾!」
蕭瑄捂著左臉,神智清明了些。
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沉下來了。
「姜楚,你敢打朕?」
鮮紅的掌印浮現在他白皙的麵皮上。
指甲劃出細長的痕,正往外滲著血。
我心中不覺快意,只覺得恨。
「陛下大可賜死我。」
「你就這樣恨朕?」
我忽然笑起來,牽動舊傷,喉嚨里都是血腥味。
「是啊,蕭瑄。」
「我恨你。」
蕭瑄波瀾不驚的眸中,閃過一絲慌亂。
從前有多愛蕭郎,現在就有多恨蕭瑄。
我闔上眼睛,不願再看。
「若是從來沒有遇見你,就好了。」
蕭瑄那晚發了好大的火。
他幾乎是怒極反笑。
「好,好,你這樣恨朕是嗎?」
「朕後宮美女如雲,難道獨獨稀罕你姜楚?」
「朕的愛,你不要,有的是人要!」
「朕是天子!」
他憤怒地從我身上爬起來。
朝門外喊了聲:「起駕,去皇后宮中!」
人卻杵在我床邊,半天沒走。
「要走快走。」打了個哈欠,有些睏倦。
「你和我裝什麼深情呢?」
11
這些日子,蕭瑄終於不再來找我。
聽聞他夜夜宿在皇后宮中。
沒過多久,皇后竟又傳出了有孕的消息。
這天,我還在撥弄著阿兄給解悶的新玩意。
皇后就氣勢洶洶地殺來了景陽宮。
身後浩浩蕩蕩一群人,有的還穿著欽天監的服制。
來者不善。
春芽想要攔人:「皇后娘娘,陛下有旨——」
被皇后身邊的宮女一巴掌扇到地上。
「賤婢。」
「這後宮之事,什麼時候輪到你來指教本宮了?」
沈玉姚撥弄著指甲上鮮紅的蔻丹。
「欽天監監正說了,宮中有人私行巫蠱之術,要害本宮腹中的孩兒。」
說著,她陰狠地抬眼看我。
「別的嬪妃那裡,本宮都帶人搜過了。」
「眼下只剩下楚嬪這兒了。」
宮女太監幾乎把景陽宮翻了個底朝天。
還是什麼都沒搜到。
皇后面上的表情,更難看了。
監正附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,皇后的眼神看向殿後的小土包。
我瞳孔緊縮。
皇后看到我臉色變了,像是驗證了她的猜想。
「給本宮挖開。」
我擋在小土包前: 「這是二皇子的衣冠冢!」
皇后冷哼了聲:「楚嬪,話當然可以這樣說。」
「但誰知道,這底下埋的到底是什麼呢?」
我張了張嘴,對上她調笑的目光,忽然失了聲。
她帶了這樣多的宮女和侍衛。
想要做什麼,我攔不住的。
「你很聰明。可惜——本宮從不嫌麻煩。」
「就是掘地三尺,也要找到證據。」
話音落下,我被幾個宮女架著。
眼睜睜地看著侍衛們一點一點,挖開那個小小的衣冠冢。
我的孩子,他若有靈,會被弄疼嗎?
小土包被挖開的時候,蕭瑄才姍姍來遲。
「陛下——」
看見他,沈玉姚簡直委屈到了極點。
她手上舉著,從那個小土坑裡挖出來的布娃娃。
布娃娃本身做得簡陋,沾上了灰塵,更髒舊了。
「楚嬪在宮中行巫蠱之術,想要害本宮腹中的孩兒。」
「被本宮找到證據了。」
不等我解釋,蕭瑄勃然大怒。
「姜楚,你的膽子是越來越大了!」
「你可知,謀害皇嗣,是大罪?」
「皇后上次不過無心之失,你竟刻毒至此!」
我的眼淚已經流乾了。
只平靜道:「我沒有。」
「你沒有?」
蕭瑄氣極反笑。
他一把抓過皇后手中那個髒污的布娃娃。
「姜楚,你自己和朕解釋,這是什麼?」
我望著他憤怒到極點的神情,扯了扯唇角:
「陛下抱走二皇子後,嬪妾夜夜驚夢。」
「春芽見嬪妾夜裡睡不安穩,做了這個娃娃讓嬪妾抱著。」
「僅是如此。」
在場所有人的表情都變了。
蕭瑄面上的表情一滯。
我指了指不遠處,那個被挖開的小土包:
「這是二皇子的衣冠冢。」
喉頭甜腥,心臟又開始泛疼。
「蕭瑄,你根本不配為人父!」
血大股大股從喉嚨里湧出來。
「楚楚,楚楚!」
「好多血 ……你怎麼了楚楚?!」
我後知後覺地垂眼。
看見自己被鮮血浸透的前襟。
蕭瑄扶住了我的胳膊,讓我不至於摔到地上。
「楚楚——」
我索性不再忍。
一偏頭,淋漓鮮血,全都吐到了蕭瑄身上。
我好恨……我好恨啊!
12
我醒來的時候,正對上蕭瑄通紅的眼睛。
他看起來守了我幾宿,面容憔悴,唇上冒出青青的胡茬。
而頭髮,已經全然白了。
我闔眼,翻了個身。
「楚楚。」
他啞聲喚我。
「你理理朕,好不好?」
疼。
我渾身都疼,不想搭理他。
「太醫說你活不久了。」
蕭瑄自顧自地說了下去,聲音有點顫。
「病入膏肓,藥石無醫。」
「為什麼?這是什麼時候落下的病症?」
「你為什麼……不告訴我?」
他竟忘了這茬。
於是我平靜地告訴他:
「你起兵的第三年,行軍路上遇見山匪。」
「我和沈玉姚被山匪劫走,那山匪頭子讓你選一個,剩下一個他帶回去做壓寨夫 人。」
蕭瑄被喚起了記憶,全然僵住了。
「然後你說,你要沈玉姚。」
我被擄回山寨,寧死不屈,受盡折磨。
我等了好久啊,蕭瑄。
那個山匪頭子叫我別傻了,乖乖從了他,少吃些苦頭。
我說我不要,我有夫君的,我夫君很快就回來救我。
然後我等啊等。
等了一天又一天,最後等來你在軍中迎娶沈玉姚的消息。
最後是阿兄拿他所有的商鋪,從山匪頭子那裡換回了我。
雖然活著回來了。
卻也損了身體,早早落下病症。
蕭瑄呆住了。
過了許久,才找回自己的聲音。
「確是朕..…對不住你。」
「朕補償你,好不好?你想要什麼,朕都答應你。」
我說:「我要出宮。」
他怔了一怔,「這個不行。」
「楚楚,換一個吧。」
「除了出宮,嬪妾別無所求。」
蕭瑄靜默片刻,忽而又絮絮叨叨說起了從前。
「萬人之上,太寂寞了。」
「不是說好,留在宮中陪著朕嗎?」
好煩。
真的好煩。
「那句承諾,是給蕭郎的。」
「不是給你的,陛下。」
蕭瑄急了:「楚楚,朕就是蕭郎!」
我盯著他,半晌,搖了搖頭。
「你不是。蕭郎從來不拿我去委曲求全。」
「朕可以解釋!」
「江山根基未穩,沈家勢大,朕不能得罪……」
可是。
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善待我。
那為什麼還要強留我呢?
為什麼不放我走?
他太貪心了,既要這個,又要那個。
註定要虧待一方。
我輕聲打斷他:「可我並不想聽。」
哪裡有這樣多那樣多的道理。
不過是,江山情重美人輕。
就這樣吧。
我好累了。
13
蕭瑄身邊的大太監帶著聖旨又來了。
我以為是來放我出宮的。
結果是晉我為妃,賜居永壽宮。
「娘娘,領旨吧。」
我搖了搖頭。
永壽宮離他的養心殿太近。
我不想住在那裡。
想著,我隨便找了個由頭打發了:
「永壽宮不種芭蕉,我不去。」
又過了幾日,蕭瑄親自來了。
「楚楚!」
蕭瑄捲起的袖子還沒有放下,衣衫上星星點點沾著泥漬。
「朕給你,種了好大一片芭蕉!」
他似乎完全忘了橫亘在我們之間的淋漓鮮血。
像個輕快少年郎,眼睛亮晶晶的,期待地和我邀功。
「楚楚,你搬過去吧。」
見我站在原地不動,他的眼睛掃向了春芽:
「朕記得你。」
他威脅般開口:「朕聽聞,就是你在愛妃身邊搬弄是非——」
我平靜道:「我去便是。陛下不必如此。」
我搬進永壽宮的第一件事。
就是命人把永壽宮外新植的芭蕉全部砍掉。
蕭瑄聽見動靜,趕來的時候。
芭蕉已經被砍得七零八落。 「姜楚,你敢!」
他厲聲呵斥,目眥欲裂。
「陛下有空討好我,不如去討好沈皇后。」
蕭瑄咬牙切齒:「這些芭蕉——你不喜歡嗎?」
我搖頭。
「不喜歡。我並不在意這芭蕉是誰所種。」
他靜了一瞬,忽然道:
「我說的不是芭蕉。」
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,依舊搖頭。
「不喜歡。」我認真道。
無論是芭蕉,還是種芭蕉的人。
我都不喜歡。
沒意思透了。
蕭瑄怔怔望著我,眼中都是破碎之色。
他還杵著不肯走。
我重複了第三遍:
「我說,我不喜歡。」
14
那日以後,蕭瑄便不怎麼敢來看我了。
他怕自己惹我不快,讓別人來陪我。
先是宣了阿兄入宮。
阿兄大概知道了我的事,一見我就紅了眼眶。
反倒是我安慰他:「生死有命,無妨。」
他沒說話,強笑著扯開了話題。
室內熏了暖香,溫暖如春。
我最近精力越發不濟,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。
「楚楚。」
半夢半醒之間,我感覺阿兄在很輕地摸著我的腦袋。
他輕聲說著些什麼。
「其實我——」
我沒聽清,迷迷瞪瞪去看他。
「嗯?」
阿兄猝然低了頭:「沒事。」
「睡吧,楚楚。」
自那以後,阿兄再也沒有在我面前失過態。
蕭瑄不知怎的,從皇后那兒要來了蕭硯。
蕭硯被提前叮囑過,不要惹我不快。
他有些怕我。
一見面,就怯怯地喊我「娘親」,和我認錯。
「娘親,阿硯錯了,別不要阿硯……」
濕漉漉的眸子一瞬不瞬地望著我,好不可憐。
我問他: 「誰讓你這樣喚我的?」
宮裡的規矩嚴,倒是很久沒聽見這樣一聲稱呼了。
蕭硯遲疑了一下,還是交代了:
「是父皇。」
他小心翼翼地覷著我的神情,嗓音稚氣。
「父皇說民間尋常人家,都是這樣喊的。」
我笑了笑:「好吧。」
15
皇城冬日多雨。
有天昏昏沉沉我在藥氣中甦醒。
望著茜紗窗外無盡的雨簾,不自覺地發獃。
忽而見著遙遙的,有個人朝著這個方向走來。
只一個模糊的影子,我就認出來了。
是蕭瑄。
他直著身子,白髮低垂。
我聽見小宮女壓低的聲音:
「娘娘服了藥,已睡下了。」
蕭瑄輕輕「嗯」了聲。
幽靈似的站在那裡,沒說話。
然後又有人影動了,是阿兄來了。
他忽然輕而快地說了句什麼,蕭瑄陡然激動起來。
我豎起耳朵,想凝神去聽,卻還是力不從心。
雨聲淅瀝,我又昏昏沉沉睡過去。
後來有一陣子雨停,我看見蕭瑄在窗下種芭蕉。
淺薄的綠意一點點填滿我的眼帘。
然而皇城冬日冷冽,沒多久葉子又凍壞了。
可他不厭其煩地,一遍又一遍地種下新的芭蕉。
「到了春日,便會好起來的。」
他頓了頓,「你和芭蕉葉都是。」
「..都會好起來的。」
我只是搖頭:「不是的。」
「芭蕉不是松柏。」
我緩了口氣,盯著袖中露出一截清瘦嶙峋的腕骨。
「柔弱之草,難抵歲寒。」
蕭瑄不敢看我。
「楚楚,不要說這樣的話。」
他聽著難過了。
可我偏要說。
「宮牆好高啊。飛鳥停在檐上,也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。」
看見他痛楚的神情,我忽然變得極為快意。
我喘了口氣,慢慢道:「我被困在這裡了。」
「是你把我害成這個樣子的,蕭瑄。」
「我不該恨你嗎?」
半晌,蕭瑄動了動唇:
「那就不要死,恨著朕。」
「永永遠遠恨著朕,不要忘記朕。」
我撥開他的手,鼻腔里發出一聲冷哼。
「你想得美。」
16
進入深冬,我的身體越來越差,開始日日咳血。
蕭瑄被嚇得方寸大亂。
血跡沾上他散開的白髮,詭艷而怪異。
他怔怔看了半晌,忽而啞聲開口:
「我後悔了。」
「是我的錯,都是我的錯。」
我理順了氣,輕輕笑:「是啊,都是你的錯。」
「那你願不願意和我一起去死?」
他脊背一僵,不動了。
「我...不該帶你來這北國霜雪之地。」
他囁嚅著,「楚楚,不說這些喪氣話。」
「我們重新來過好不好?」
我闔著眼,心中平靜得掀不起一絲波瀾。
沒意思透了。
太醫熬的藥越發苦了。
這日,我服完藥,伸手去抓罐子裡的蜜餞吃。
一旁的蕭瑄默不作聲地端來盤甜糕。
我順手拿了一塊。
難以言喻的怪異味道在口腔中彌散開來。
胃裡翻江倒海,我撫著胸口,往下壓了壓。
蕭瑄望著我,眼神有些期待。
「好吃嗎?是朕親手做的。」
壓不住,「嘩」的一聲全吐出來了。
蕭瑄慌了,作勢要來扶我。
「楚楚,楚楚?!」
我拍開他的手:「別碰我,噁心!」
他尷尬地站在原地,滿臉的不知所措。
我瞧著他的樣子,忽又輕聲細語:
「我同你開玩笑的。」
「只是甜糕放冷了,吃著不舒服。」
蕭瑄眼中一亮,「我、那我馬上再去做!」
等他端著一盤熱騰騰的糕點過來時,我只隨便掃了一眼。
「沒胃口。」我說。
蕭瑄強笑著:「吃一口吧,楚楚,朕、我做了兩個時辰….」
我煩得很。
眼睛都不抬,抬手打翻了他手上的盤子。
白瓷碎了一地,精緻的糕點七零八落。
我說:「現在不用吃了。」
蕭瑄呆呆地看著滿地的狼藉。
阿兄自然沒辦法帶我走的。
我們都心知肚明。
就算如今是富甲一方的商人,也沒辦法帶走皇帝的嬪妃。
我們只能坐在這四四方方的宮牆裡,回憶著曾經的好光景。
他絮絮講著我幼時的趣事。
我彎著眼睛,笑了又笑。
直到太監來催,說時辰已到,阿兄該回了。
我才戀戀不捨地鬆開阿兄的袖擺。
「明日,阿兄還來麼?」
未等阿兄說話。
身後,忽然傳來一道陰惻惻的聲音:
「他明日不會來了。」
「這次進宮,乃是朕格外恩准。」
我回頭,蕭瑄正從花架後緩緩踱步而出。
不知道待在那裡,偷聽了多久。
他扯了扯唇角,笑意嘲諷。
「姜楚,朕從前倒是從來不知道,你與他這般情深意重。」
「你若想要實現什麼心愿,該來求朕才是。」
10
阿兄走了。
蕭瑄被我嘲諷了一通,也怒氣沖沖地走了。
這天夜裡,又淅淅瀝瀝下起了雨。
半夜,殿門被人猛然破開了。
黑暗裡,有人摸到了我的榻邊。
潮濕的熱氣吹拂在我耳廓上。
那人壓在了我的身上。
春芽尖叫著要跑去喊人,被踹到地上。
「楚楚。」
燭火亮起,映出蕭瑄有些疲憊的面容。
他身上都是潮濕的水汽。
難聞的酒味鑽進我的鼻尖。
蕭瑄抬手抱住我,夢囈似的喃喃:
「不要再說氣話了,你不知道朕聽了那些話,難過得很。」
「和朕和好,好不好?」
說著,他的手在我腰間亂摸。
竟是要解我的衣帶。
我抬手,甩了他一耳光。
「滾!」
蕭瑄捂著左臉,神智清明了些。
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沉下來了。
「姜楚,你敢打朕?」
鮮紅的掌印浮現在他白皙的麵皮上。
指甲劃出細長的痕,正往外滲著血。
我心中不覺快意,只覺得恨。
「陛下大可賜死我。」
「你就這樣恨朕?」
我忽然笑起來,牽動舊傷,喉嚨里都是血腥味。
「是啊,蕭瑄。」
「我恨你。」
蕭瑄波瀾不驚的眸中,閃過一絲慌亂。
從前有多愛蕭郎,現在就有多恨蕭瑄。
我闔上眼睛,不願再看。
「若是從來沒有遇見你,就好了。」
蕭瑄那晚發了好大的火。
他幾乎是怒極反笑。
「好,好,你這樣恨朕是嗎?」
「朕後宮美女如雲,難道獨獨稀罕你姜楚?」
「朕的愛,你不要,有的是人要!」
「朕是天子!」
他憤怒地從我身上爬起來。
朝門外喊了聲:「起駕,去皇后宮中!」
人卻杵在我床邊,半天沒走。
「要走快走。」打了個哈欠,有些睏倦。
「你和我裝什麼深情呢?」
11
這些日子,蕭瑄終於不再來找我。
聽聞他夜夜宿在皇后宮中。
沒過多久,皇后竟又傳出了有孕的消息。
這天,我還在撥弄著阿兄給解悶的新玩意。
皇后就氣勢洶洶地殺來了景陽宮。
身後浩浩蕩蕩一群人,有的還穿著欽天監的服制。
來者不善。
春芽想要攔人:「皇后娘娘,陛下有旨——」
被皇后身邊的宮女一巴掌扇到地上。
「賤婢。」
「這後宮之事,什麼時候輪到你來指教本宮了?」
沈玉姚撥弄著指甲上鮮紅的蔻丹。
「欽天監監正說了,宮中有人私行巫蠱之術,要害本宮腹中的孩兒。」
說著,她陰狠地抬眼看我。
「別的嬪妃那裡,本宮都帶人搜過了。」
「眼下只剩下楚嬪這兒了。」
宮女太監幾乎把景陽宮翻了個底朝天。
還是什麼都沒搜到。
皇后面上的表情,更難看了。
監正附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,皇后的眼神看向殿後的小土包。
我瞳孔緊縮。
皇后看到我臉色變了,像是驗證了她的猜想。
「給本宮挖開。」
我擋在小土包前: 「這是二皇子的衣冠冢!」
皇后冷哼了聲:「楚嬪,話當然可以這樣說。」
「但誰知道,這底下埋的到底是什麼呢?」
我張了張嘴,對上她調笑的目光,忽然失了聲。
她帶了這樣多的宮女和侍衛。
想要做什麼,我攔不住的。
「你很聰明。可惜——本宮從不嫌麻煩。」
「就是掘地三尺,也要找到證據。」
話音落下,我被幾個宮女架著。
眼睜睜地看著侍衛們一點一點,挖開那個小小的衣冠冢。
我的孩子,他若有靈,會被弄疼嗎?
小土包被挖開的時候,蕭瑄才姍姍來遲。
「陛下——」
看見他,沈玉姚簡直委屈到了極點。
她手上舉著,從那個小土坑裡挖出來的布娃娃。
布娃娃本身做得簡陋,沾上了灰塵,更髒舊了。
「楚嬪在宮中行巫蠱之術,想要害本宮腹中的孩兒。」
「被本宮找到證據了。」
不等我解釋,蕭瑄勃然大怒。
「姜楚,你的膽子是越來越大了!」
「你可知,謀害皇嗣,是大罪?」
「皇后上次不過無心之失,你竟刻毒至此!」
我的眼淚已經流乾了。
只平靜道:「我沒有。」
「你沒有?」
蕭瑄氣極反笑。
他一把抓過皇后手中那個髒污的布娃娃。
「姜楚,你自己和朕解釋,這是什麼?」
我望著他憤怒到極點的神情,扯了扯唇角:
「陛下抱走二皇子後,嬪妾夜夜驚夢。」
「春芽見嬪妾夜裡睡不安穩,做了這個娃娃讓嬪妾抱著。」
「僅是如此。」
在場所有人的表情都變了。
蕭瑄面上的表情一滯。
我指了指不遠處,那個被挖開的小土包:
「這是二皇子的衣冠冢。」
喉頭甜腥,心臟又開始泛疼。
「蕭瑄,你根本不配為人父!」
血大股大股從喉嚨里湧出來。
「楚楚,楚楚!」
「好多血 ……你怎麼了楚楚?!」
我後知後覺地垂眼。
看見自己被鮮血浸透的前襟。
蕭瑄扶住了我的胳膊,讓我不至於摔到地上。
「楚楚——」
我索性不再忍。
一偏頭,淋漓鮮血,全都吐到了蕭瑄身上。
我好恨……我好恨啊!
12
我醒來的時候,正對上蕭瑄通紅的眼睛。
他看起來守了我幾宿,面容憔悴,唇上冒出青青的胡茬。
而頭髮,已經全然白了。
我闔眼,翻了個身。
「楚楚。」
他啞聲喚我。
「你理理朕,好不好?」
疼。
我渾身都疼,不想搭理他。
「太醫說你活不久了。」
蕭瑄自顧自地說了下去,聲音有點顫。
「病入膏肓,藥石無醫。」
「為什麼?這是什麼時候落下的病症?」
「你為什麼……不告訴我?」
他竟忘了這茬。
於是我平靜地告訴他:
「你起兵的第三年,行軍路上遇見山匪。」
「我和沈玉姚被山匪劫走,那山匪頭子讓你選一個,剩下一個他帶回去做壓寨夫 人。」
蕭瑄被喚起了記憶,全然僵住了。
「然後你說,你要沈玉姚。」
我被擄回山寨,寧死不屈,受盡折磨。
我等了好久啊,蕭瑄。
那個山匪頭子叫我別傻了,乖乖從了他,少吃些苦頭。
我說我不要,我有夫君的,我夫君很快就回來救我。
然後我等啊等。
等了一天又一天,最後等來你在軍中迎娶沈玉姚的消息。
最後是阿兄拿他所有的商鋪,從山匪頭子那裡換回了我。
雖然活著回來了。
卻也損了身體,早早落下病症。
蕭瑄呆住了。
過了許久,才找回自己的聲音。
「確是朕..…對不住你。」
「朕補償你,好不好?你想要什麼,朕都答應你。」
我說:「我要出宮。」
他怔了一怔,「這個不行。」
「楚楚,換一個吧。」
「除了出宮,嬪妾別無所求。」
蕭瑄靜默片刻,忽而又絮絮叨叨說起了從前。
「萬人之上,太寂寞了。」
「不是說好,留在宮中陪著朕嗎?」
好煩。
真的好煩。
「那句承諾,是給蕭郎的。」
「不是給你的,陛下。」
蕭瑄急了:「楚楚,朕就是蕭郎!」
我盯著他,半晌,搖了搖頭。
「你不是。蕭郎從來不拿我去委曲求全。」
「朕可以解釋!」
「江山根基未穩,沈家勢大,朕不能得罪……」
可是。
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善待我。
那為什麼還要強留我呢?
為什麼不放我走?
他太貪心了,既要這個,又要那個。
註定要虧待一方。
我輕聲打斷他:「可我並不想聽。」
哪裡有這樣多那樣多的道理。
不過是,江山情重美人輕。
就這樣吧。
我好累了。
13
蕭瑄身邊的大太監帶著聖旨又來了。
我以為是來放我出宮的。
結果是晉我為妃,賜居永壽宮。
「娘娘,領旨吧。」
我搖了搖頭。
永壽宮離他的養心殿太近。
我不想住在那裡。
想著,我隨便找了個由頭打發了:
「永壽宮不種芭蕉,我不去。」
又過了幾日,蕭瑄親自來了。
「楚楚!」
蕭瑄捲起的袖子還沒有放下,衣衫上星星點點沾著泥漬。
「朕給你,種了好大一片芭蕉!」
他似乎完全忘了橫亘在我們之間的淋漓鮮血。
像個輕快少年郎,眼睛亮晶晶的,期待地和我邀功。
「楚楚,你搬過去吧。」
見我站在原地不動,他的眼睛掃向了春芽:
「朕記得你。」
他威脅般開口:「朕聽聞,就是你在愛妃身邊搬弄是非——」
我平靜道:「我去便是。陛下不必如此。」
我搬進永壽宮的第一件事。
就是命人把永壽宮外新植的芭蕉全部砍掉。
蕭瑄聽見動靜,趕來的時候。
芭蕉已經被砍得七零八落。 「姜楚,你敢!」
他厲聲呵斥,目眥欲裂。
「陛下有空討好我,不如去討好沈皇后。」
蕭瑄咬牙切齒:「這些芭蕉——你不喜歡嗎?」
我搖頭。
「不喜歡。我並不在意這芭蕉是誰所種。」
他靜了一瞬,忽然道:
「我說的不是芭蕉。」
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,依舊搖頭。
「不喜歡。」我認真道。
無論是芭蕉,還是種芭蕉的人。
我都不喜歡。
沒意思透了。
蕭瑄怔怔望著我,眼中都是破碎之色。
他還杵著不肯走。
我重複了第三遍:
「我說,我不喜歡。」
14
那日以後,蕭瑄便不怎麼敢來看我了。
他怕自己惹我不快,讓別人來陪我。
先是宣了阿兄入宮。
阿兄大概知道了我的事,一見我就紅了眼眶。
反倒是我安慰他:「生死有命,無妨。」
他沒說話,強笑著扯開了話題。
室內熏了暖香,溫暖如春。
我最近精力越發不濟,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。
「楚楚。」
半夢半醒之間,我感覺阿兄在很輕地摸著我的腦袋。
他輕聲說著些什麼。
「其實我——」
我沒聽清,迷迷瞪瞪去看他。
「嗯?」
阿兄猝然低了頭:「沒事。」
「睡吧,楚楚。」
自那以後,阿兄再也沒有在我面前失過態。
蕭瑄不知怎的,從皇后那兒要來了蕭硯。
蕭硯被提前叮囑過,不要惹我不快。
他有些怕我。
一見面,就怯怯地喊我「娘親」,和我認錯。
「娘親,阿硯錯了,別不要阿硯……」
濕漉漉的眸子一瞬不瞬地望著我,好不可憐。
我問他: 「誰讓你這樣喚我的?」
宮裡的規矩嚴,倒是很久沒聽見這樣一聲稱呼了。
蕭硯遲疑了一下,還是交代了:
「是父皇。」
他小心翼翼地覷著我的神情,嗓音稚氣。
「父皇說民間尋常人家,都是這樣喊的。」
我笑了笑:「好吧。」
15
皇城冬日多雨。
有天昏昏沉沉我在藥氣中甦醒。
望著茜紗窗外無盡的雨簾,不自覺地發獃。
忽而見著遙遙的,有個人朝著這個方向走來。
只一個模糊的影子,我就認出來了。
是蕭瑄。
他直著身子,白髮低垂。
我聽見小宮女壓低的聲音:
「娘娘服了藥,已睡下了。」
蕭瑄輕輕「嗯」了聲。
幽靈似的站在那裡,沒說話。
然後又有人影動了,是阿兄來了。
他忽然輕而快地說了句什麼,蕭瑄陡然激動起來。
我豎起耳朵,想凝神去聽,卻還是力不從心。
雨聲淅瀝,我又昏昏沉沉睡過去。
後來有一陣子雨停,我看見蕭瑄在窗下種芭蕉。
淺薄的綠意一點點填滿我的眼帘。
然而皇城冬日冷冽,沒多久葉子又凍壞了。
可他不厭其煩地,一遍又一遍地種下新的芭蕉。
「到了春日,便會好起來的。」
他頓了頓,「你和芭蕉葉都是。」
「..都會好起來的。」
我只是搖頭:「不是的。」
「芭蕉不是松柏。」
我緩了口氣,盯著袖中露出一截清瘦嶙峋的腕骨。
「柔弱之草,難抵歲寒。」
蕭瑄不敢看我。
「楚楚,不要說這樣的話。」
他聽著難過了。
可我偏要說。
「宮牆好高啊。飛鳥停在檐上,也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。」
看見他痛楚的神情,我忽然變得極為快意。
我喘了口氣,慢慢道:「我被困在這裡了。」
「是你把我害成這個樣子的,蕭瑄。」
「我不該恨你嗎?」
半晌,蕭瑄動了動唇:
「那就不要死,恨著朕。」
「永永遠遠恨著朕,不要忘記朕。」
我撥開他的手,鼻腔里發出一聲冷哼。
「你想得美。」
16
進入深冬,我的身體越來越差,開始日日咳血。
蕭瑄被嚇得方寸大亂。
血跡沾上他散開的白髮,詭艷而怪異。
他怔怔看了半晌,忽而啞聲開口:
「我後悔了。」
「是我的錯,都是我的錯。」
我理順了氣,輕輕笑:「是啊,都是你的錯。」
「那你願不願意和我一起去死?」
他脊背一僵,不動了。
「我...不該帶你來這北國霜雪之地。」
他囁嚅著,「楚楚,不說這些喪氣話。」
「我們重新來過好不好?」
我闔著眼,心中平靜得掀不起一絲波瀾。
沒意思透了。
太醫熬的藥越發苦了。
這日,我服完藥,伸手去抓罐子裡的蜜餞吃。
一旁的蕭瑄默不作聲地端來盤甜糕。
我順手拿了一塊。
難以言喻的怪異味道在口腔中彌散開來。
胃裡翻江倒海,我撫著胸口,往下壓了壓。
蕭瑄望著我,眼神有些期待。
「好吃嗎?是朕親手做的。」
壓不住,「嘩」的一聲全吐出來了。
蕭瑄慌了,作勢要來扶我。
「楚楚,楚楚?!」
我拍開他的手:「別碰我,噁心!」
他尷尬地站在原地,滿臉的不知所措。
我瞧著他的樣子,忽又輕聲細語:
「我同你開玩笑的。」
「只是甜糕放冷了,吃著不舒服。」
蕭瑄眼中一亮,「我、那我馬上再去做!」
等他端著一盤熱騰騰的糕點過來時,我只隨便掃了一眼。
「沒胃口。」我說。
蕭瑄強笑著:「吃一口吧,楚楚,朕、我做了兩個時辰….」
我煩得很。
眼睛都不抬,抬手打翻了他手上的盤子。
白瓷碎了一地,精緻的糕點七零八落。
我說:「現在不用吃了。」
蕭瑄呆呆地看著滿地的狼藉。
 喬峰傳 • 41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41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5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5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6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6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31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31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0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0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16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16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0次觀看 卞德江 • 50次觀看
卞德江 • 5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11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11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12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12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4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5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5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0次觀看